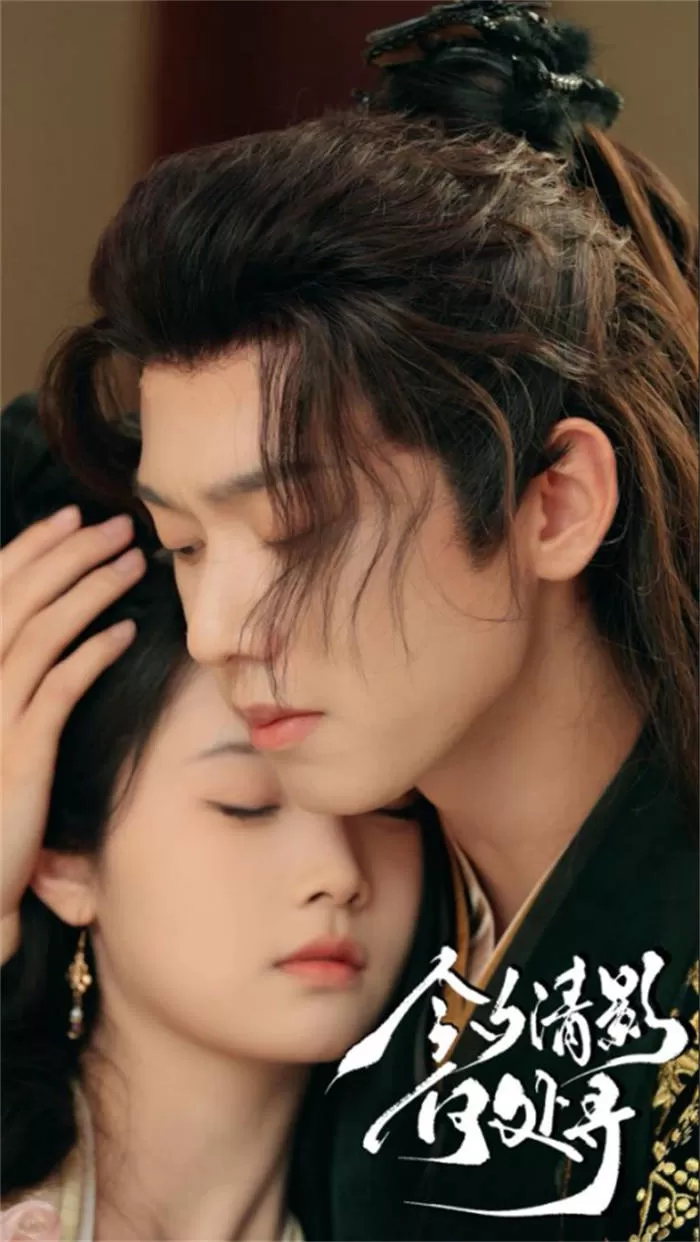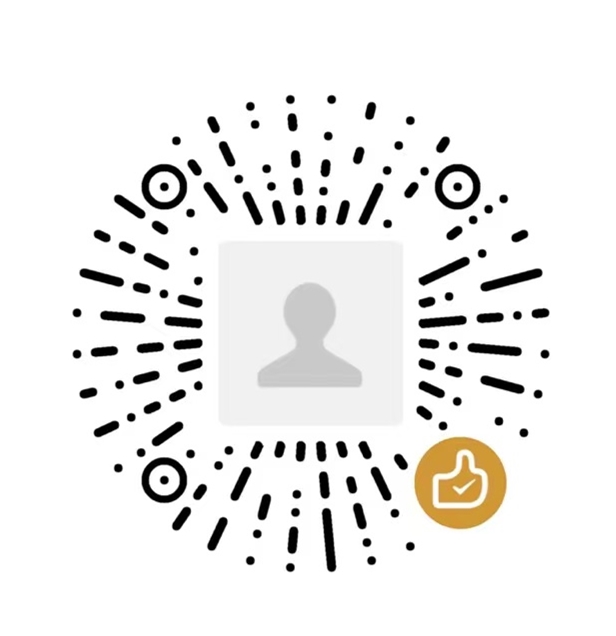媒体报道的人。她在成长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很多困惑,但她在思维方式上天然的开明,以及为了让她未来可以不用再“活在他们的游戏里”所带来的动力,给了两位“母亲”莫大的帮助。
《小巷人家》就更加典型,黄玲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,正好形成对照组。儿子虽然也会在妈妈吃饭不上桌的时候察觉到愧疚与异常,但他很容易就放弃了抵抗。当亲戚家小孩想住到自己家来的时候,儿子的第一反应也是学习爸爸的慷他人之慨,“无私奉献”是他理解中第一顺位值得学习的价值。反观只有女儿拥有不一样的视角,因为女儿本身也是重男轻女家庭环境中的受害者,她会被奶奶点名要去照顾卧床的她,这也让她更能理解母亲在维护孩子时的立场。
女儿的存在,让女性友谊或女性共同体中出现了传承与希望,更加丰富了女性“重组家庭”所能表达的意涵。孩子的“早熟”也能让观众意识到,具备相似的视角或许并不取决于年纪或成熟与否,只在于女性的社会身份本身,真的有太多属于“第二性”的隐秘无奈,只消多看一眼便能体会。
女性话语有多难?
即便找到了一种可能,但想要发扬光大或者找到新的女性话语依旧很难。
“现在的影视依旧如此,要不就是男人的故事,女人是附庸,是妈妈和女儿,为了展示男人的不容易、男人的绊脚石、男人的善良和男人还有人性。要不然就是女人已经忍无可忍,要杀人要复仇,以及女人在谈恋爱。”早在《好东西》上映之前,邵艺辉就曾在公开场合精准地概括当代女性题材创作的困境,只是因为近期电影热映,这段发言又被翻了出来不断传播。
简单来说,在如今仍然由男性占绝对主导的影视行业里,女人在作品中往往只有“圣母”与“复仇”两种形态,同时还一定是“恋爱脑”。无论是从前偶像剧对“恋爱脑”的浪漫化还是如今对“恋爱脑”的抵制,都是男性视角下将女性角色视作客体而形塑的结果。
这会让不少女性创也感到困惑,因为不管是按照传统的影视叙事逻辑还是“性转版”的逻辑,都会让人感觉不太对劲。要做到“不玩他们的游戏了”,邵艺辉自己也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答案。
《小巷人家》的创作相对来说更有局限性,并非正午阳光突然觉醒,女性意识断层式暴涨,而更有可能的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,女性互助有现实层面上极强的必要性。创只需遵循它的纪实性,便可以自然帮助找到超越那个年代的先锋性。毕竟,80年代的先锋性有诸多体现之处,也不仅仅在女性领域。
包括在海外的影视作品中,女性互助“重组家庭”的情况也不少见,但大多数的呈现都更加直给,也同时具有一定程度的现实迫切性。比如很多作品本身讲的就是拉拉的故事,或者是像《同妻俱乐部》一样被男性伤害从而结成同盟的故事。包括前不久的日剧《住宅区的两人》,两个女性重组家庭,其实是基于无人养老的无奈。
所以,像《好东西》这种没有明确现实迫切性的创作会变得更难,因为这两个女性角色没有非要紧密结合的必要。她们本身就有自己不错的生活,单纯因为彼此的认同与情感联结而重组在一起,需要创极其强悍的编剧功力才能让人信服。
比如令不少观众印象深刻的,给母亲的日常家务劳动拟音的段落,既实现了视听设计,同时实现了“主妇的无形劳动应该被看见”的议题表达,没啥理解门槛,还松弛有趣。
如果编剧能力实在达不到,就算怎样探索叙事角度,最终呈现出来的作品也很难做到“好看”。即便做成如今这个样子,依然有部分不和谐的声音认为,两位女主角的中产身份过于真空,从阶级眼光去审视太过悬浮不接地气,可见编剧这项工作的众口难调程度。
即便已经做成了豆瓣9.1,目前《好东西》的票房和预售数据仍然不容乐观,点映至今也仅突破3000万,最终票房落点很难比《爱情神话》高出太多。数据的冷淡展现出了与舆论场奔走相告截然不同的画面,这说明对这类女性话语感到振奋的同温层受众基数实在太少,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还有太多意识上等待觉醒的人群。
当《芭比》横空出世的时候,国内都在期许我们自己也产生这样的女性主义作品,但显然当下的舆论整体水位距离《芭比》还甚远。令人惊喜的是,在2024年的年尾,中国影视在不同创作带不约而同地诞生了新的女性话语,这种柔性话语不以斗争作为目标,只有轻微的刺痛感,甚至幽默感强过反抗性。
就像宋佳和闫妮饰演的妈妈不必是完美的妈妈一样,女性主义从来都不是在追求塑造完美女性,而是创造让她们得以自由呼吸的空间。《好东西》就是这样一方近乎真空的纯然空间——这绝不是放弃斗争了,我们只是,不想玩父权制游戏了。
找到女性话语很难,让好不容易出现的女性话语存续也很难。这当然是男性话语长期以来浸泡的结果,人们更想要新奇刺激的故事,作为欲望投射的角色。连女性创有时都很难突破窠臼,更遑论普通观众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值得买 » 🉑《好东西》与《小巷人家》中国影视自己的芭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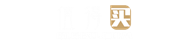 值得买
值得买